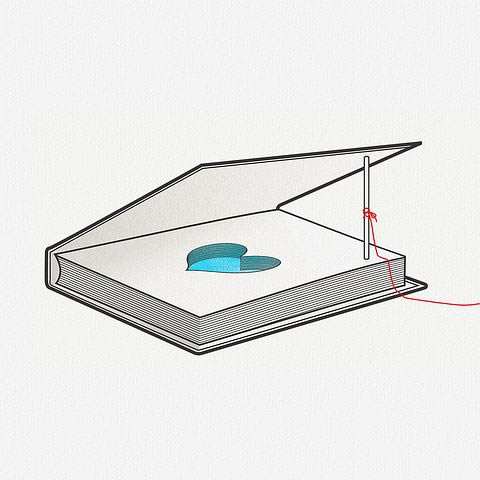陨落的“中国帕瓦罗蒂”的故事_陨落的“中国帕瓦罗蒂”完整版简短
情感故事2022-9-8 1:59:39阅读:次
前方是绝路,幸福在拐角。
我的座右铭是“生命在于静止”,高中三年,从不参加学校的运动会。
高二那年,人家参加运动会,我在广播室里播报各班来稿。那次,运动会结束,团委书记王浩找到我,说要带我去见一个人。
我跟着他走进一间办公室,里面坐着一位女老师,大约30岁。她看到我,激动地站了起来。
“他就是你要找的学生,叫李咏。”王浩介绍说。
经她自我介绍,我才知道她是我们学校的音乐老师,姓刘。高中没有音乐课,所以我险些没见过她。她从广播里听到我的声音,觉得我是棵唱歌的好苗子。
“你的声音很好,愿意跟我学唱歌吗?”她望着我,满眼热切。
“愿意啊。”
她脸上掠过一丝惊喜,但很快就岑寂下来,对我说:“唱歌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学的,需要许多先决条件,比如声带条件。”
“您刚才不是说我声音很好吗?”
“听上去是很好,但我还要带你去医院搜检。”
于是,我和她一路到了医院,挂了口腔科的号。
最终的诊断结论是:“声带闭合很好,宽、厚、长,像瓷砖一样平滑。”
刘老师对我注释说:“如果声带闭合不好,有缝隙,声音就是嘶哑的。声带的宽窄、薄厚,决定了你声音的粗细、音域的高低,表面的平滑程度决定了声音的质量。”
很快,我开始上课了。每周二、四两天,每次练习两个小时。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实践,我的喉咙打开了,每次音域扩展演习都能向上爬半个音阶,自然音域达到了12度。连老师都惊呆了,她发自心里地欣喜啊,终于等到了一个得意门生。
一年以后,我已经能够完整地唱完哈萨克族民歌《嘎哦丽泰》,这是音乐学院声乐系一年级的演习曲目。
我和刘老师另有一个约定,也可以说是一个共同的理想——高三毕业,我报考上海音乐学院,她为我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支持。我们为了这个理想太投入了,偏偏忘记了一件事。
我比较晚熟,已经高二了还没经历变声期。正在我理想着成为中国的帕瓦罗蒂时,一天早晨醒来,我突然之间之间之间发现自己失音了。
母亲赶忙把我送到医院,医生的诊断是“声带小结”,原因可能是长期用声不当或用声太过。
接下来很长时间,我厂都住在医院里。
时间一天一天地溜走,距离上海音乐学院的专业课考试越来越近了。每日早上醒来,我都试着对自己说一声:“你好!”却发不出声儿。
直到两个月以后,那天早上,我从床上坐起来,习惯性地却又不抱任何希望地对自己说了声:“你好!”
话一出口,我吓傻了。
居然收回了声音……而且,根本不是我的声音!
这声音听起来是低沉的,嘶哑的,而已往我的声音是高高悬在上方的,响亮的。
我这是怎么了?
几天以后,我又去音乐教室练声。我一次又一次地试唱,高音再也上不去了,只剩下中高音。我的心冰凉冰凉,全完了。一年的努力,就这样付诸东流。梦碎的不只是我,另有我的老师。
之后,我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考上广院之前我又去医院搜检了一下声带。诊断结论和已往一模一样:“宽、厚、长,像瓷砖一样平滑。”老天助我,劫后余生……
我的座右铭是“生命在于静止”,高中三年,从不参加学校的运动会。
高二那年,人家参加运动会,我在广播室里播报各班来稿。那次,运动会结束,团委书记王浩找到我,说要带我去见一个人。
我跟着他走进一间办公室,里面坐着一位女老师,大约30岁。她看到我,激动地站了起来。
“他就是你要找的学生,叫李咏。”王浩介绍说。
经她自我介绍,我才知道她是我们学校的音乐老师,姓刘。高中没有音乐课,所以我险些没见过她。她从广播里听到我的声音,觉得我是棵唱歌的好苗子。
“你的声音很好,愿意跟我学唱歌吗?”她望着我,满眼热切。
“愿意啊。”
她脸上掠过一丝惊喜,但很快就岑寂下来,对我说:“唱歌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学的,需要许多先决条件,比如声带条件。”
“您刚才不是说我声音很好吗?”
“听上去是很好,但我还要带你去医院搜检。”
于是,我和她一路到了医院,挂了口腔科的号。
最终的诊断结论是:“声带闭合很好,宽、厚、长,像瓷砖一样平滑。”
刘老师对我注释说:“如果声带闭合不好,有缝隙,声音就是嘶哑的。声带的宽窄、薄厚,决定了你声音的粗细、音域的高低,表面的平滑程度决定了声音的质量。”
很快,我开始上课了。每周二、四两天,每次练习两个小时。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实践,我的喉咙打开了,每次音域扩展演习都能向上爬半个音阶,自然音域达到了12度。连老师都惊呆了,她发自心里地欣喜啊,终于等到了一个得意门生。
一年以后,我已经能够完整地唱完哈萨克族民歌《嘎哦丽泰》,这是音乐学院声乐系一年级的演习曲目。
我和刘老师另有一个约定,也可以说是一个共同的理想——高三毕业,我报考上海音乐学院,她为我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支持。我们为了这个理想太投入了,偏偏忘记了一件事。
我比较晚熟,已经高二了还没经历变声期。正在我理想着成为中国的帕瓦罗蒂时,一天早晨醒来,我突然之间之间之间发现自己失音了。
母亲赶忙把我送到医院,医生的诊断是“声带小结”,原因可能是长期用声不当或用声太过。
接下来很长时间,我厂都住在医院里。
时间一天一天地溜走,距离上海音乐学院的专业课考试越来越近了。每日早上醒来,我都试着对自己说一声:“你好!”却发不出声儿。
直到两个月以后,那天早上,我从床上坐起来,习惯性地却又不抱任何希望地对自己说了声:“你好!”
话一出口,我吓傻了。
居然收回了声音……而且,根本不是我的声音!
这声音听起来是低沉的,嘶哑的,而已往我的声音是高高悬在上方的,响亮的。
我这是怎么了?
几天以后,我又去音乐教室练声。我一次又一次地试唱,高音再也上不去了,只剩下中高音。我的心冰凉冰凉,全完了。一年的努力,就这样付诸东流。梦碎的不只是我,另有我的老师。
之后,我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考上广院之前我又去医院搜检了一下声带。诊断结论和已往一模一样:“宽、厚、长,像瓷砖一样平滑。”老天助我,劫后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