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里怀旧的爱情的故事_8月里怀旧的爱情完整版简短
情感故事2022-8-28 0:14:05阅读: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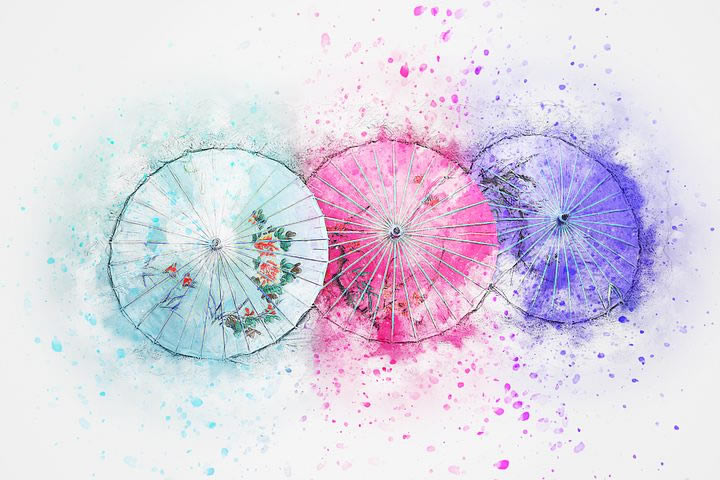
恩诺去了深圳的一家电脑公司,北大的高材生到哪里都有人要的。
小卉上的只是一个普通的学校,学的是历史。她想,哪个公司昏了头会要一个历史系的学生呢?除非这个公司想知道秦始皇除了修长城还做了什么!每日挤在地铁里去找工作时,小卉想,自己也许真生错了年代,速食时代的人们,哪里还管得了已往?
所以,碰到了举着一本线装书看的天籁时,她呆了一下。对面的须眉,格子衬衣、棕色的裤子,背着一个很大的牛仔包,正在看一本《芥子园画图》,那是她中学时看过的。再过两天,他又看一本极黄的线装书,像是稍微一抖就能把岁月的风霜抖出来。
看来,喜欢怀旧的不仅仅是她小卉啊。
他的名字,是从封面上看到的。天籁。很古典的名字,像他的人,恩诺就没有这样的气质,一副盘算机业新宠的样子,喜欢西服革履地在镜子前说,放心吧,几年之内我就成为张旭日,那时周围也会美女如云啊。
小卉说,呸,周恩诺,你别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我不美吗?
你美吗?周恩诺说,五分姿色三分打扮两分聪明而已,以后,我要找个李嘉欣那样的美女,养养我的眼。知道他是开玩笑,小卉依然不悦,这样的男人,真不知有了钱会怎么样?
碰到天籁的第10天,小卉找工作已快筋疲力尽,外面的温度快40度了,买了一张三块钱的地铁票在地铁里往返逛着,翻看着自己的简历和各个公司的招聘广告,心里灰蒙蒙的,不知要如何把这个8月度过。
所以有时候就对恩诺发脾气,说为他为爱情两肋全插满了刀,而恩诺说,你别觉得多委屈,你可以回你的小城,这世界谁离开谁都能活。
本以为他会说着甜言蜜语,谁知却冷冷地说着这样不咸不淡的话,怎么刚进了社会就变得这样?以前追自己的时候像个大情痴一样,这样一想,心就凉了下去。
进地铁的时候,她感觉头有些晕,这才想到,从早晨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一点东西喝过一口水,怕是要中暑吧?正想着,才看到那个穿着格子衬衣的男人就软软地倒了下去,眼前一黑,什么都看不到了。
醒来时,在一个男人怀里。男人有淡淡的香气,像是用过香水,清凉的那种,她睁开眼,说了三个字:对不起。
地铁轰隆隆地开走了,只有他和她坐在站台的椅子上,他拧开一瓶冰水,递过一个三明治,然后说,太热的天尽量少出来跑。
她心里一酸,眼泪差点落下来。这种话,恩诺一句也没说过。
再次在地铁里碰到,她和他会相视一笑,从那瓶冰水和那个三明治开始,她已经把他当成朋友。
而他,依然常常拿一本旧书在地铁里读着,抬起眼看她时,眼里露出淡淡的笑。
小卉躲开他的眼光,她知道,这种男人是对她有致命的诱惑的。
而此时,她终于找到了一个公司上班,和历史没有干系,负责收收文件打扫卫生,下了班和恩诺一路到租的房子里缠绵,给他做红烧带鱼和青菜鸡蛋面。那是一个三十多平方米的小屋,没有空调,她常常会热得整夜整夜不能入睡,8月,这么热腾腾地黏连着,恩诺还黏人,总是没完没了,事后却又沉沉地睡去,根本没有问过她的工作和感受。
倒是地铁里的天籁有一日抬起头来问,找到工作了吧?小卉很感激地摇头,他又说,在深圳能站住脚就不错,慢慢来,总会好起来的。
自始至终,小卉没有问过他做什么工作,碰到的时候,他们相互点摇头,她看他往返换的线装书,有一次居然看到他看的是李渔文集,能看李渔的人得多聪明多有聪明啊,恩诺喜欢看的是《黑客帝国》,她就喜欢看那些绝望的电影,比如《惊情四百年》,一个女人为了自己爱的男人变成为僵尸,比如《胭脂扣》,那样的悲情总让她与恩诺的爱情无法联系起来。
她总觉得她和恩诺的爱情少了什么。但地铁里的天籁却让她有一种温暖。
常常,他们只有10厘米的距离,甚至,她能感觉到他的呼吸,但是她不敢抬头,在这个有些湿热和暧昧的8月里,她无缘无故地觉得那么欢乐又那么悲伤,偶尔的眼光交流,她会避开,再不避开,她怕自己又会晕倒。
难道自己爱上了这个叫天籁的须眉吗?不过二十多天前在地铁里碰到,甚至说过的话不过10句。但她喜欢看他出了地铁迎着风走的背影,有点孤独有点寥寂,有一次,她正呆呆地看着,他突然之间回了一下头,然后展颜一笑,那笑里,竟然有着那么多让人回味的内容。
再回家,她从前面搂住恩诺,恩诺,我们结婚吧。
恩诺说,别闹了,我们才刚站住脚,怎么可能?
她的眼泪,泅进恩诺的衬衣里,恩诺说,神经兮兮的,怎么了?掰开她的手,一个人去打电动游戏。
有5天,她没有去坐地铁,一个人换公共汽车,正热的天里,站在艳阳下,想着地下铁里看线装书的人,突然之间想掩面。
8月的最终一天,她又去了地下铁。
见到他,他说,来了?怎么好多天没有来?病了?
小卉呆呆地看着他。他也看着她,像是有一生一世那么长,其实不过几秒钟吧。
我等了你5天,我想通知你一件事儿。
不要说。小卉说,不要通知我。她心里里挣扎着,我有男友了。她说。
他笑了,我下周就走了,去法国,谢谢你让我在这一个月碰到你。
因为每次与你的相遇,你都像一阵清风吹在我心头,另有,你那件紫色的裙子非常漂亮。
小卉都忘记什么时候穿了紫色裙子,而面前的须眉却记得她的紫色裙子。
眼泪浮上来时,地铁到站了,他走出去,在车开门的刹那,他突然之间大声地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小卉的眼泪哗地流下来,车门关闭了,她在地铁里嚷着:我叫小卉,我叫小卉。
所有人全看着她,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儿笑着说,姐姐,我叫大米。全车厢的人都笑了。
那是他们最终一次相见。
小卉出了地铁时才发现,秋风像是来了,从腿下钻出来,一阵凉似一阵,短裙子在风中显得那么萧瑟。她抱了抱肩,觉得有点冷,她知道,这冷,全然不是天气的缘故。
小卉的8月,像烟花一样散去,甚至留下的痕迹极少,如果有,也是那眷注的眼光和线装书的味道,另有那个有了温度的名字:天籁。
6年过后,小卉已在香港的一家公司做主管。6年是多长?她倒真是不晓得,但6年的改变却那样真实,她一向努力,读了MBA,又来了香港,和恩诺分了手,是因为半年过后小卉在自己家的床上看到了另一个女孩儿子,恩诺老总的闺女(daughter),用小卉的话来说,不过三分姿色的一个女子,却让恩诺对5年的感情说了再见。
过后,她又谈了若有若无的频频恋爱,开始的时候淡,结束的时候更是觉得寡味,她再都没有地铁里那份爱和忧伤,常常,她会想到那个看线装书的须眉。
之后,她到香港,过着单身白领丽人的生活,一个人去中环逛商店买东西,去书店也喜欢看那些古旧的书,日子一天天过下去,香港的爱情不似《倾城之恋》中的香港了,之后碰到了美国返来的德汀,德汀说,小卉,我们做个同居情人可好?
小卉说,德汀,我只想找个人天荒地老。
德汀说,小卉,你像是不是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你白白用这么好的包和香水,另有你那巴黎的粉底,也没遮住你的那份古典,可惜,能浏览古典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大家都会在找一份快餐爱情吃,你邃古怪了。
小卉轻轻弹掉手上的烟灰说,德汀,你要相信,无论什么时候都有相信地久天长的人。
那日去中环和一个客户谈生意,约了在蓝夜咖啡吧,那里气氛是极浪漫的,她喜欢那种淡雅和清幽,那里另有好多印刷精美的杂志,铜版纸,许多前卫而时尚的东西浮在纸上,非常鲜艳的文字和图片。
等待客户的时候,她常常会随意翻翻那些杂志。那天也是如此,突然之间,她的目光停住。
是一张鲜艳的画。那地铁里站着的女子,那穿紫色的女子,那眼光里有绝望和爱的女子,不是小卉,又是谁?好久好久,她的眼泪落了下来,画底下是作品的名称——《小卉的8月》,仓促的泪似大水决堤,作者是压在心底里那么多年的名字:天籁。
原来他是画家。
另有一行文字,是天籁写的。
他写到这幅画的创作历程:那年8月,在深圳地铁里,在故乡的最终一个月里,我碰到一个清凉的女孩儿子,她每日穿行在地铁里,有一种古典的美和忧伤。
但我与她擦肩而过。因为小卉的8月,是她一个人的8月,不曾有我。
她的眼泪落入那幅画上,那落下的眼泪说明了一切:在小卉的8月里,始终有你啊。
只是他与她一向在错过,错过了8月,又错过了今生,就像他提起过的那件紫色裙子,小卉再都没有穿过,一向挂在衣柜里飘来荡去,不是不想穿,是再也舍不得。
- 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