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自己去成长,自己去成功》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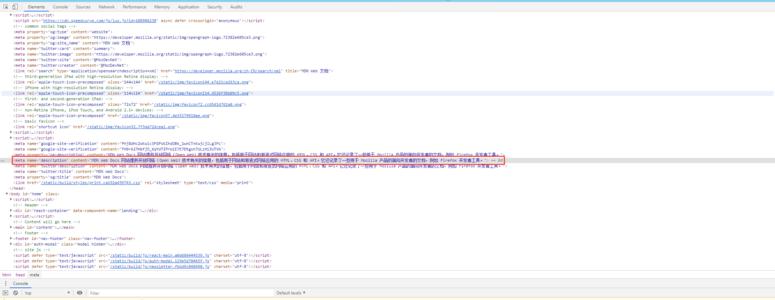
午饭后,和往常一样,我躺在沙发上看报纸,用眼角的余光看着大门,欢迎女儿放学回家。但是我的心突然颤抖了,我今天不用等我女儿了,因为前天我把她送到了离家300多英里的集中营。这不是一个真正的集中营,而是一个有60年历史的“牧场”?山地夏令营”。每年暑假,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在那里接受魔鬼训练。世界顶级大师伊萨巴拿马、马友友、林昭亮和秋彦都来自那里。音乐营占地200多英亩,散布着从马厩改建的宿舍。屋顶是铁做的。因为马厩本来不高,所以改成了两层,所以你可以用手够到天花板。此外,窗户出奇的小,房间只能转过来。人们可以想象夏天阳光普照时天气会有多热。更可怕的是营地里的规则——典狱长会像“狱卒”一样在早上7点钟一个接一个地敲门,直到学生们开门才会停下来。你必须在7: 30步行去数百英尺外的餐馆吃饭。八点半整,我必须回到我的小房间,开始练习钢琴。舍监一整天都在走廊里巡逻,敲门警告没有听到钢琴演奏的人。别动,然后“记住”;只要有两点被记录下来,它们就会在周末被禁止。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我那娇惯的女儿,以为她是小公主的女儿,要进去。在进入营地之前,我反复问她,可以吗?暑假呆在家里有多舒服,为什么要受苦?我七周内不能回家。我通常不允许家人来访,我打不通电话,我甚至不能带我的电脑,我甚至不能谈论乡愁,真遗憾!女儿想都没想,于是她转过身说:“我想去!”我进入营地的那天,气温是35摄氏度。我偷偷溜进她的房间偷看了一眼,浑身是汗。当我出来时,我问她是否会回家。她转过身说,“不。”当她离开时,她的女儿正在排队支付体检表格,挥手让我们离开。我偷偷看了看她是否在哭。她甚至没有红眼睛。她说她很兴奋。我上了公共汽车,慢慢地离开了校园。我不停地回头看,但那个声称不愿放弃父母的小女儿却背对着我们。事实上,在美国有许多这样的“集中营”,包括音乐、体育、文学和科学。碰巧“一个人愿意战斗,一个人愿意受苦”,有那么多年轻人,尽最大努力进去接受虐待。从我女儿被接纳到夏令营,我经常想到“待在一个女人的大课间休息时”和“待在一个孩子的大课间休息时”。当我的儿子进入哈佛并把他送到那里时,我离开时哭了。他不是也“看见”我离开了吗?他们如此无情是因为他们很兴奋能离开父母。或者是因为前面有太多的挑战,“受苦的人没有权利悲观”。就像我离开家一段时间,独自来到美国一样。在机场,甚至学生们都哭了,但我没有哭,因为我必须忍受前方的艰辛。他们呆在家里,过着平静的生活,但我成了一个流浪者。但是为什么所有的年轻人都想漂泊,梦想成为陌生人,感到孤独和危险是一种酷,这是一种自然的冲动吗?正是这种动力使人类的祖先能够走出最早的非洲,走向全世界,甚至登上月球,相信有一天他们会到达火星。也正是这种动力使得王子和公主们不顾父母的哭喊,走出了她父亲的城堡,跳上了马,飞驰而去。我知道中国的父母在强迫他们的孩子。我没有反对他们,并告诉他们不要努力工作。相反,我告诉他们“成功需要成功,正如成长需要成长。”让他们强迫自己,而不仅仅是等待他们的父母和老师在背后推波助澜。这两天,每当我走过女儿的房间,看到她的公主床,我就想哭。然而,我知道,我那两斤半重的臂膀再也支撑不住她千里之行的生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