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来珈华祭剑魂的故事 何来珈华祭剑魂完整版简短
一、遗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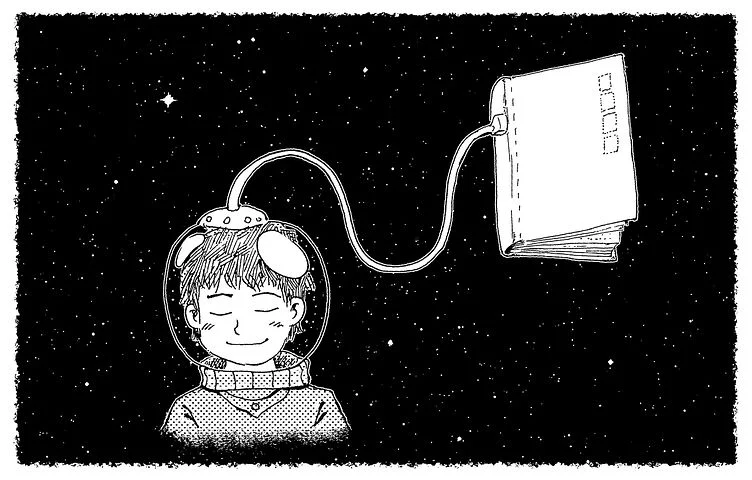
——斜阳染金甲,漫天血红。
这片战后的残地上,放眼望去尽是茫茫倒地的躯体,空气中血腥扑鼻。江子清躺在同伴的尸体上直视着绯红的天空,滚烫的泪便从眼角滑了出来。
为什么他没有死,同来的元国八万将士都永远地沉睡在了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仅剩他还残存着呼吸感受这生不如死的气息。
然而就在他泪眼模糊之时,满目绯红的天幕上绽放了一朵苍白的光束,一个身影从天边走了过来。
江子清用他断筋的右手拄着长枪从一片尸首中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他决不许可被别人看到自己像个死人一样躺在地上。
那个身影近了,江子清才看清了对方独特的装束。那人穿一身月白长袍,前襟与袍角上镶一道血红的边,金色的长发如水般飘盈而起,左手空垂,右手倒提一柄长剑,赤裸的双足每走一步便有一朵烈焰开在地上。
江子清亲眼看着那人走到离自己三丈远时,左手撩起前襟单膝向他跪下。
“无尚尊贵的风情大神,”白袍人低垂着头,跪在一片尸首中,萧瑟的风扬起那一袭月白长袍,金色的发丝撕扯着天边的云:“请接纳我虔诚的叩拜。”
“什么人?”江子清的心没来由地揪了起来,他甚至不敢相信能看到有人从天空上走下来,竟然还给自己下跪。
白袍人徐徐抬起头来,这张脸便是江子清永生也忘不掉的,那不是倾国倾城所能形容的,也许是天地间最完美的一张脸,连创世神都会为自己创造的这张脸而满足地叹息。
她是个气质郁闷的女子,有些苍白的脸上带着淡漠清肃的表情,那双深碧色的眸子便仿佛海底般神秘而深沉。
“我是珈华。”表情依旧淡漠,珈华直视着面前半身染血的将士语气生硬地开口,“请通知我您的愿望。”
“愿望?”江子清非常迷茫地看着跪地之人,若不是自己方才已经历过生死之战,怕是现在早已膜拜在此女人脚下了,因为那分明是超脱世人的样貌与装束。
绝望地扫过满地尸首,虽然不知道女子的来历,但已无所谓生死的江子清无限悲怆地说:“如果可以,我想将元国旌旗插到尚国都城之上。”
将本国旌旗遍插敌都城墙,这是一个临死将士的最终愿望,不是生活安逸,不是高官厚禄,而是报国立功。
珈华徐徐地垂下头去,玫瑰一般的唇角浮出一抹奇异的笑:“世间一切皆因您的存在而存在。”
二、断剑
——月华袭人,彩绢舞空。
九天宫阙之上,那是谁的一双眼睛在望着他。这样郁闷,仿佛一触即碎的琉璃碧玉,萦绕着无尽的梦幻与情丝。
终究记不起名字。
胸口一阵抽痛,江子清从梦中醒来,那双眼睛在深沉的影象中明艳地存在着。
“子清,快来见过你的先生。”房外传来父亲(father)的轻呼,江子清定了定神从床上下来穿好衣靴,轻推门扇走入正厅。
江丞相一见儿子便上去拍他:“还不快拜见皇上特派来教授你学业的楚先生。”
江子清还没搞晓畅怎么回事便被父亲按着跪了下去:“学生江子清拜见楚先生。”
“免礼,起身罢。”正堂座榻上的先生轻笑了一声。
江子清听了觉得新鲜,起身一瞧便吃了莫大一惊。正坐在榻上轻呷茗茶眯眼浅笑的楚先生竟是个女子,而她的脸却正是珈华。
“莫要惊异。”楚先生放下茶盏,起身向江子清走去。虽是着了青柳的长衫,束了碧玉的发髻,但她依旧是金色的发,深碧的眸,右手倒提长剑,穿了长靴的双足走起来便有超凡脱俗的轻盈。
左手执起江子清的袖子,楚先生笑着将他领到堂外望向漫天眩烂的阳光,一双眼睛弯得尤如月牙:“明年昔日,便是你愿望成真之时。”
这天迎春盛放满枝,扑天遍地一片鹅黄。江子清站在花丛中,从迎春谢牡丹开,牡丹枯雏菊盛,半年里他用断了十七柄剑,但他的手一向不曾放下。
与楚先生对立站在一片枯草原野中,江子清看着插在地上仅剩的三柄剑紧皱双眉。半年里楚先生教他如何调兵遣将,如何一招制敌,原先所插的二十柄剑已折断了十七柄。
“拔出你的剑。”塞外的疾风将楚先生一身青衫猎猎扬起,练剑时的她的声音总是一贯地清冷。
江子清握紧其中一把剑柄手臂一震便拔了出来,看向对面立在一片枯草中衣袂飞舞的楚先生,她的武器便是右手那柄倒提的长剑。那是一柄独特却坚固的剑,剑身月白,剑柄赤红,楚先生便持着剑尖将剑柄拄在地上,这样使剑的人永远杀不死对手,却更轻易被杀。
可楚先生就是这样姿态从容地倒提着长剑击断了江子清十七柄剑。
“叮”地一声脆响,江子清手上第十八柄剑断了。这十八柄皆是名剑,每一柄都经过千锤百炼堪称极品,却在与楚先生的剑相交时轻易崩断。
“我通知过你,当自己赖以生存的武器被敌人折断时,一定要立即寻找另一种武器来保卫自己。”楚先生将长剑拄在地上,表情肃穆,“哪怕是你誓死的目光,哪怕是你残缺的身体,都要让敌人知道你不会屈服。”
江子清永远记得楚先生那张清绝人世的脸上郁闷而萧瑟的表情,每次练剑都仿佛置身真实战场。
终于在江子清的第二十柄剑折断时,天空上飘下细小的雪花来。楚先生倒拄着长剑立在风雪中仰望天空,江子清曾无数次见到这种姿态的楚先生,他总会想到她从天而降的那一瞬。白袍飞舞,金发轻舞,倒提长剑,赤足之下生烈焰。
“先生,”江子清走已往站到楚先生身边与她一同仰望飞雪的天空,“可以通知我这柄剑的名字么?”
楚先生深碧色的眸子颤了一下,悲伤从深处泛滥出来,她徐徐阖上双眼,长久沉默后转身离去:“总有一日,你会知道它的名字。”
楚先生远去的身影在漫天飞舞的白雪中这样凄然,长剑的剑柄在地上划出一条火龙,模糊了江子清的视线。
三、春寄
——自古多情伤离别,水暖花开又一春。
迎春再次盛放时,江子清便披上了战甲,楚先生亲自为他系上艳红的战袍,然后站在城墙上目送他在不计其数的将士中骑着战马驰骋远去。
楚先生遥望着那一条如洪流的人群,唇角浮出了少有的弧度:“一切都将如你所愿。”
虽然没有随军出征,但楚先生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她知道此次十万战将气势汹涌地来到尚国都城下,但城外所种百亩“春寄”却成为牵引他们灵魂的锁链。
“春寄”是一种毒花,它会在阳光强盛之时倾情绽放,香气世上最盛,却会让所闻之人窒息而亡。
风起了,浓郁的香气远播开去,已行至尚国都城外绵延数里的十万将士陶醉于这美妙的气息时已经悠然倒地,双目惊诧地瞪着,似是不晓畅自己为何会死去。
仿佛梦魇一般,大片大片的将士倒下去,江子清大声叫着他们的名字,依然挽不回他们远去的英灵。又宛如是在眨眼之间,十万将士齐齐倒地,没有鲜血,没有刀剑,就那样安静地死去。
为什么他没死,为什么依然和一年前一样,所有人都死去了唯独只剩他。江子清开始恐惧感,就在他看到尚都大门轰然大开之时。
栗红的钢铁之门徐徐敞开,走出来的却不是身披战甲的浩荡敌军,而是五个布衣之民,只有五个而已。
他们远远地就朝江子清膜拜,求他饶他们不死。
“你们的将军呢!他应该出来保护你们!”江子清大吼的声音听起来如此悲壮。
五个人将身后的城池指给江子清看:“死了,全城的人都死了。”
江子清全身猛然一颤,完全不相信的他在疯狂地翻遍了整座城过后站在城墙上终于徐徐跪倒。
空的,这是一座空城。
那五个人通知他,一年前城外一晚之间便长出百亩花苗,因为太过美好所以没有人去伤害它们。这一年里它们发芽,拔节,生枝,直到一月前突然之间之间之间就绽放了。只需一瞬间城外变成为花的陆地,香气扑鼻那一刻,全城的人便在不知觉间失去了呼吸。
尚都就变成为一座死亡空城。
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花,又是谁在一晚间种了百亩。
直到一个身着白袍的女子从城外走来救起他们五人,并要他们在此为一月后到来的人打开城门。
“那女子是不是一头金发,倒提长剑?”江子清揪住其中一人的领口急问,而那人却泪流满面地指着城墙之外,低泣道:“她来了。”
江子清猝然转头望去,城外踏着遍地沉睡的将士之身,一个身着月白长袍的人走了过来,金发与衣袂翻飞在空中,鲜花映着她清绝的容颜,左手垂空,右手倒提长剑,赤裸的双足踩在地上便生出一朵烈焰。
“你的愿望实现了。”珈华立在城下仰望上去,依旧是初见时郁闷的气质。
“不!这不是我所期望的!”江子清站在城墙上对女子大吼,声音哽咽,“我要的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哪怕我粉身碎骨也不要他们一切死在这种卑劣的毒花下!”
他怎么能够容忍十万将士全数死去只为成就他一个愿望,这根本不是他所希望的战争。
“岁月可以见证,没有任何一份功绩可与您的尊贵相比。”珈华单膝跪倒在一片尸首中,目光悲悯,“这个世上,即便所有的人都死去了您也必将立于无尚之位。”
四、赐婚
——黄袍裹身,公子如玉。
江子清背着一生的歉责接受皇上的封赐,虽然尚都不是他亲手攻克,虽然那十万英灵从此长眠于地下。
除了天外清肃的风没有人知道因果,所以喜娘便不绝于江府门前,每日空上门说亲的喜 娘总是不知疲倦。江子清作为男方被许多女方上门说亲在事先竟成潮流,不只因他年轻官高,平日里一身黑衣的浊世公子模样更令无数少女芳心暗许。
然而梦中那双眼睛却无论如何也忘不掉,仿佛是穿越几千年的眷恋,在门外的风中重复无数次花开花落,只为等待他的一声召唤。
可那是谁?为什么他记不起了呢?
“通知我你的愿望。”梦中依旧听到那个清冷的声音。
沉睡的江子清徐徐淌下了热泪,因为他记起了那十万出生入死的兄弟,再也不想任何人受伤,于是他呢喃地呓语:“与我爱的人相守白头。”
我爱的人,琴音萦绕之外是九天宫阙上那一双悲怆的眸子。
“一切将会如你所愿。”
广阔的皇家猎场上,一队华服锦衣的须眉骑坐在骏马上,扬鞭奔驰,一头梅花鹿正在骑队的追赶下惊慌而逃。英武的男人们齐齐搭箭引弓,所谓逐鹿天下,便只在此一射之中。
江子清拉了个满弓,却还未瞄准时只见一支红翎响箭已经从旁咆哮而过了。
何来珈华祭剑魂(2)
远方正逃窜的梅花鹿猛地一个趔趄倒在地上便起不来了。
好箭法!江子清心中不禁赞叹。
骑队之首,身着龙袍的皇上哈哈大笑起来:“朕生了个巾帼女将呀!”
“父皇打算怎么犒赏儿臣呢?”骑队过后策马赶来一红衣女子,她侧过头来对众人嫣然而笑。
江子清看了那张脸过后惊得掉了手上的长弓,娇俏的笑靥,飞舞的红袍,这分明是珈华。
“你想要何犒赏?”皇上宠爱地笑着。
红衣的公主揽了缰绳驱马来到江子清身边,两只桃花一样的眼睛笑得眯了起来:“听闻江大人府中说亲的女子不绝门槛,大人觉得哪个最漂亮?”
江子清知是珈华在戏弄他,便苦笑道:“天下女子,哪一个也比不上公主十分之一的美貌。”
公主一听笑得双颊绯红,歪着头对江子清道:“那我嫁你可好?”
皇上的圣旨下给了江子清,将琴笙公主指配于他,望两人相敬如宾,白头偕老。
江子清仰头望向漫天星空中那轮如眸瞳的月牙,这双于九天之上凝望他的眼睛无论怎样也找不到的,那只是一个梦而已。清酒一饮而尽,胸膛是火辣辣地疼,然而他却说不出究竟是为何而疼。
“一向找不到对么?”身后有人为自己披了一件大氅,江子清一侧头便看到那张超凡脱俗的脸。
“公主。”江子清发现公主有些绯红的脸颊,一身的酒气,也不知她究竟是饮了多少酒。
“我也一向在找他。”公主仰头有些迷醉地望着月夜,嘴角怆然一笑,“听我讲个故事行么?”
江子清安安静静地摇头,然后公主就走出凉亭来到湖边扶着围栏叹息道:“那是一个很古老的相传,老到所有人都把它遗忘了,只有我还记得。讲的是九天之上最俊美的风情大神,他在与敌人战斗时为了保护自己的剑不被崩断,而将自身灵力一切注入剑体,最终被迫坠入世间没有了踪迹。”
“你所说的风情大神,是我么?”江子清记起初见时她跪在他面前叫他“风情大神”。
公主侧头看着江子清,苦笑:“我希望你是。”
江子清叹息着摇头:“公主找错人了。”
夜风乍起,卷起湖面上潮湿的水气沾了两人一身。江子清裹紧了身上的大氅:“公主现在退婚还来得及。”
公主拾手捋了捋被风吹乱的金发,嘴角带着意味深长的笑:“我必须要实现你的愿望。”
江子清怔了怔,他的愿望“与我爱的人相守白头”,心头那个影子似乎在酒液的洗涤下逐步清楚起来,从一双眼睛开始往外扩散,鼻子,嘴唇,眉梢,发际。当整张脸都拼凑起来时,江子清被自己吓到了。
那赫然是珈华的脸。
五、红衣
——遍身罗绮慈母念,怎堪浊泪染嫁裳。
将布尺比在身上量尺寸,用手掌捺着袖子的宽度,母亲的每一个举措都如此认真,那双浑浊的眸子甚至看不清布尺上的刻度。
江子清说让裁缝来量制,母亲却要亲手为他做婚袍,虽然眼睛看不太清针线,可她脸上却满是笑意:“我儿光宗耀祖做驸马了,为娘一定要为你做一件合体的婚袍。”
江子清转过身去眼眶有些发烫,曾经多少年母亲满含期望的目光鞭策着他去立功立业,现在他功高伟业之时母亲已经在不知不觉间苍老了。
直到大婚那天,母亲早早起了身为他穿上那一袭大红的婚袍,胸前挂上大红花,看着儿子这一身装束母亲拭了拭眼泪,嘴上却笑得合不拢:“好,我儿穿着很合身。”
跨上白马,江子清领着迎亲的队伍往皇宫去了,父母亲长久地立在门外清风中,仿佛是儿子出嫁一般。
喧天的锣鼓响彻了整个皇宫,艳红的花瓣铺天盖地洒下来,空气中尽是花蜜的香甜气息。当被人群簇拥着的新娘从内室走出来时,江子清险些以为自己在梦中,因为他突然之间之间之间意识到大红盖头下的那张脸根本不属于这个世间。然而当他牵住公主的手时,心中竟是这样满足,仿佛这个信念被搁浅了几千年终于成真实一般,花开花落几千年的等待只为牵住她的手。
扶着公主进了金銮喜轿,江子清驱马引领队伍回到江府。这条路仿佛有无限的长,走了好久都没有到家门口。直到一个江府仆人跌跌撞撞地赶来扑倒在江子清的马蹄边:“少爷!为什么还不回府!”
喧天震响的锣鼓声中江子清也未听见那仆人究竟在哭嚎着什么,只是看清了他浑身的鲜血。
江子清纵身下马扶住仆人只见他涕泪皆下地哭嚎却听不见他说了些什么,于是他朝身后大呵一声:“停!”震天的喧闹声顿时消逝,只剩仆人的哭喊:“老爷和夫人到死都没等到您回府啊}”
幽静的长街上,仆人的哭声仿佛千万把匕首一般硬生生剜进了江子清胸膛。没有涓滴犹豫,江子清翻身上马,疯了一般向江府飞驰而去。
他身后迎亲队伍中,那一顶金銮喜轿被人从里面掀开帘子,一个挑起盖头向外张望的倩影映入众人眼底,虽然只是惊鸿一瞥却无人能忘记那张倾城素颜。
江子清还不待白马停稳,他整个人已经飞身而下了,江府挂了大红灯笼的门口躺着两个仆人,喉咙正往外渗着血。
江子清一撩前襟冲进了府内,首先映入瞳仁的是大片大片的白色,挂在檐角的喜绸与满地的血泊交织成杂乱的油彩。府内杂乱无章躺在地上的仆人,他们身上还系着大红的喜绸。
江子清踉跄着身子步入正堂,然而堂中这一幕却是他几生几世无法遗忘的。父亲被一柄剑贯穿腹部钉在椅背上,他仰着头,双目欲裂地瞪着屋顶,仿佛正看到凶手一般。
母亲和仆人一路躺在地上,殷红的血依旧不住地从她背上涌出来,她的手直直地伸向堂外,似乎在临死前还想握住未归之人的手。
江子清抱住母亲已经冰凉的身体咬紧了牙却依然止不住地流下热泪,他想大叫“父亲母亲”,可他们永远也听不到了。
“少爷!您终于返来了!”堂外一个仆人匍匐着大哭起来,“江府上下七十二条人命都被那个女人杀害了!”
“那个女人有一头金色头发,倒持着长剑,走一步就在地上起一团火。”仆人到最终已经泣不成声了。
江子清徐徐握紧双拳,白袍金发,倒提长剑,赤足之下生烈焰,就是这样一个女子杀了他在这个世上所有的亲人。
而这个女子却是他昔日将要迎娶进门的新娘。
六、葬魂
——一愿浮萍,二愿韶华,三愿葬仙魂。
“普天之下,即便一切都土崩瓦解,您也必将端坐于高榻之上。”堂外传来了清冷的声音,江子清抬头不可思议地看到珈华一身凤冠霞帔向堂内走来,她右手倒提长剑,双足赤裸踩过一个又一个尸体在上面燃起一团火焰。
“为什么?”江子清尽力压抑着胸中怒火,低沉地吼道,“为什么要杀死他们?”
“任何一个世人都没有资格站在您身边,更没有资格做您的父母。”珈华来到江子清面前,表情淡漠地看着他。
“来到这个世间,你究竟想做什么。”江子清轻轻放下母亲站起身来的一瞬,不解地看着红衣女子。
“来满足你的愿望。”珈华绝不躲避地迎着江子清灼灼的目光,“你不是要与你爱的人相守白头么?”
“可他们已经死了!”江子清终于怒吼起来,“这世上不只有你,他们都是我所爱的人你知道吗?”
是的,七尺男儿的爱人不只是他的妻子,包括他的亲人,兄弟。
珈华有些不解地看着江子清,突然之间就笑了,依然那张清绝天下的容颜,现在看来却有令人不安的惊骇:“那么通知我你的下一个愿望罢。”
江子清绝不犹豫地转手拔出了钉在他父亲身上的那柄剑,用楚先生曾教他的招数刺向了珈华。想都没想,在第一时间寻找可以自卫的武器,这也是楚先生教他的。
“叮”地一声脆响,江子清的剑在与那柄奇剑交锋时依然折断了。
“第三个愿望是杀了我么?”珈华冷笑着眯起眼睛,声音严寒,“我曾经一向通知你,当你的武器被敌人折断时一定要立即寻找另一种武器,哪怕是你的目光,你的身体,都要让敌人知道你没有屈服。”
江子清的眼眶湿润起来,曾经楚先生教过他的所有,昔日竟要用来对付她。但这是必须的,第三个愿望哪怕拼尽他的生命也要亲手实现。
江子清口掌向珈华劈了已往,就那样两手空空赤手空拳地劈向了珈华——哪怕是残缺的身体,都要让敌人知道你没有屈服。
看到江子清这一行为,珈华不易察觉地笑了,是欣慰而悲切的笑。
珈华扬起了长剑。
然而江子清却顺势握住了直指他喉咙的剑柄,是的,那是剑柄,永远被珈华倒提在外的剑柄,永远不会刺破皮肤,伤害对方的剑柄。
江子清握住剑柄的那一刻他感觉自己从来没有这样力量强盛过,于是他使尽了全身的力气,用楚先生教过他的招式控着长剑,将剑尖硬刺向了珈华的胸膛。
眼看着手上所持的长剑已失控地向自己刺来,珈华有七种不同的方式躲开,但她没有,就那样亲眼看着长剑刺入自己的胸膛。
“噗”地一声血肉破裂之音,长剑从珈华背上穿透出来。
珈华抬头看向江子清冷漠的脸,终于写意地笑起来,仿佛千百年来一向含苞的花朵儿在春雨过后婉然绽放:“很好,你终于学会用剑了。”
江子清不想抬头正视她的脸却忍不住看了一眼,然而仅此一眼他便再也移不开目光,珈华苍白的脸上两行清泪长划而下,她的身体开始变得虚无缥缈。
“你一定很迷惑。”珈华无力地支撑着身体,虚弱地笑着,“我现在可以通知你这柄剑的名字了。”
江子清眼前的红衣女子越发缥缈起来,然而她却一向保持着温柔的笑,她说:“这柄剑,名为珈华。”
“当年是您为了保全我而不惜自己坠入凡世,所以只要您将我这只剑魂亲手埋葬便会规复灵力了。几千年来寻找着您的灵魂,倒提剑铎,为的就是方便您,手持剑柄亲手刺穿我的胸膛。所以现在您的第三个愿望实现了。”
珈华的身体险些透明,只有那双悲伤的眸子还在眷恋地望着江子清,她轻轻地唱起挽歌:“醒来吧,我无尚尊贵的风情大神。看那玫瑰在为你绽放,看那清风在为你起舞。天边袭来的日光,您的影象就在这光芒中永远不被磨灭。无论生生世世,我将为您守候。”
堂中一扇窗户被风拂开,盛大的阳光透了出去洒在江子清一身婚袍上。
所有的影象都会在这一刻鲜活起来,绝世无双的灵力齐齐汇聚到握剑的手掌中,虚无的人形被窗外的风一吹便飘散开来,化成无数闪亮的星点,宛如萤火虫(glowworm)一般绕着这个持剑的须眉转了几圈,纷纷向着门外不同的方向飞去了。
只剩那一柄红光流转的珈华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