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合欢树》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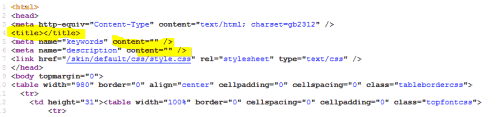
10岁时,我在作文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我母亲那时还年轻。她急着要告诉我她自己的情况。她说她小时候作文写得更好。老师甚至不相信她能写出这么好的作文。“老师找了个家来问,家里的大人是否帮忙了。那时我可能还不到十岁。”当我听到这些,我很失望,故意笑着说:“也许吧?你说可能还没有是什么意思?”她解释道。我假装根本没注意她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这让她很生气。然而,我承认她很聪明,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她正在给自己做一条蓝底白花的裙子。20岁时,我的腿残疾了。除了为别人画鸡蛋之外,我想我应该做点别的。我改变了几次主意,最终想学习写作。我母亲那时并不年轻。对于我的腿,她开始有白发在她的头上。医院已经明确表示目前没有办法治愈我的病。然而,我母亲的全部心思仍然集中在治疗我的疾病上,到处找医生,询问民间疗法,并花很多钱。她总能为我找到吃的喝的,或者洗的,敷的,烟和灸的奇怪的药。“别浪费时间了!没用的!”我说。我只想写小说,好像那东西能把残疾人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再试一次。你怎么知道不尝试就不行?”她说每次她虔诚地举起希望。然而,我对我的腿失望了很多次。最后一次,我的裤裆被烧伤了。医院的医生说它太悬了。对瘫痪的病人来说,这几乎是致命的。我不太害怕。我觉得死了更好。我很高兴死去。我母亲被吓了几个月。她日夜注视着我。她一换衣服,就说:“为什么这么热?我还在往外看!”幸运的是,伤口愈合了,否则她会发疯的。后来她发现我在写一本小说。她对我说,“那就好好写。”我听说她最终不顾一切地想要治好我的腿。“我年轻的时候,也最喜欢文学,”她说。“当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也想过写作,”她说。"你年轻的时候,作文不是得了第一名吗?"她提醒了我。我们都尽力忘记我的腿。她到处为我借书,并催我在雨中或雪中去看电影。她给了我希望,就像她过去给我找医生,询问民间疗法一样。30岁时,我的第一部小说出版了,但是我的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了。几年后,我的另一部小说获得了另一个幸运奖。我妈妈已经离开我7年了。获奖后,更多的记者前来采访。每个人都是善意的,认为我不容易。然而,我只准备了一组词,这让我感到不安。我摇了摇我的车,躲了出去,坐在小公园里安静的树林里,心想:为什么上帝会早点叫我妈妈回来?迷迷糊糊中,我听到了答案:“她的心太苦了。上帝看到她无法忍受,所以他叫她回来。”我的心得到了些许安慰。我睁开眼睛,看到风吹过树林。我开车离开那里,在街上游荡,不想回家。母亲去世后,我们搬回家了。我很少去我妈妈住的小院子。这个小院子在一个大院子的尽头。我偶尔骑车去院子,但我不想去那个小院子,说我不方便手拉手进去。院子里的老太太们仍然把我当成他们的儿孙,尤其是当她们认为我没有母亲的时候,但是她们什么也不说。他们只是聊天,指责我不经常去。我坐在院子中间,喝着我老板的茶,吃着贾茜的甜瓜。有一年,人们终于提到了他们的母亲:“去小院子看看。你妈妈种的金合欢今年开花了!”我心里直打哆嗦,但我还是说手推车进出太难了。这个小组停止了谈话,开始谈论其他事情。谈到住在我们以前住的房子里的年轻夫妇,那个女人刚刚生了一个儿子,孩子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盯着窗户上的树影。我没想到这棵树还活着。那一年,我妈妈去劳动局给我找了份工作。当她回来时,她在路边挖出了一个新出土的含羞草。她认为这是含羞草,把它种在花盆里,但结果却是一棵金合欢树。母亲总是喜欢那些东西,但那时她的心不在这里。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了一口气,不愿意把它扔掉。她仍然让它在陶罐里生长。第三年,合欢又长出了叶子,并且茁壮成长。我妈妈高兴了很多天,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她经常去工作,不敢粗心大意。又过了一年,她把合欢树从花盆里搬出来,种在窗户旁边的地上。有时候她会说,我不知道这棵树会开多久。又一年后,我们搬回家,我们的悲伤让我们忘记了那棵小树。与其在街上闲逛,我想看看这棵树更好。我也想看看我妈妈住的房间。我一直记得有一个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他没有哭,也没有大惊小怪,只是盯着树影。是那棵金合欢树的影子吗?院子里只有那棵树。